2019年11月27日上午10:00,永利集团70周年校庆暨音乐学系“秋冬学术月”系列活动讲座第20讲在永利集团4号教学楼203录播教室举行,讲座由音乐学系主任叶明春教授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主任王清雷先生带来了题为“‘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讲座。
讲座之前,王清雷首先宣读了一份关于刘家洼墓地出土音乐考古新材料的使用声明。对于音乐考古新材料的使用权和共同研究成果的发布权,要无条件听从考古队的安排。没有考古队的授权,不能私自公开使用和发表,也不能将任何材料转发给第三方,这是音乐考古田野工作的职业操守与原则。在王清雷的讲座中凡是涉及陕西澄城刘家洼墓地所出乐器的资料,均来自公开发表(纸媒、电视台媒体、网媒等)过的文章、视频等材料,不涉及没有发表过或未经授权使用的新材料。随后,王清雷正式开始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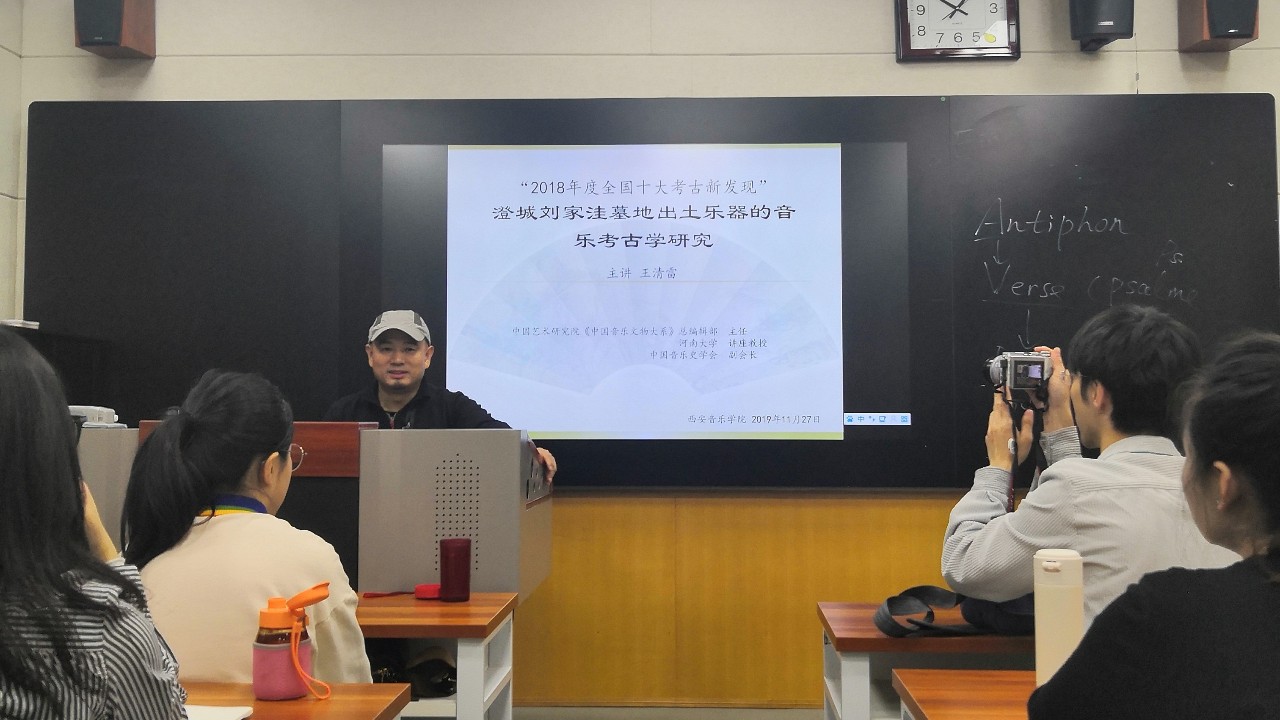
刘家洼东周遗址位于陕西澄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北,为春秋早中期芮国后期的一处都邑遗址,该遗址入围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功入选2018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队重点发掘了该遗址的两处墓地,出土了大量乐器,均出自东I区墓地的三座大墓(M1、M2和M3)中。三座墓葬均遭严重盗扰。M1出土乐器有编甬钟2套(现存10件)、编磬2组(现存10件)、建鼓以及钲。M2出土乐器有编甬钟2套(现存12件)、编磬(现存6件)、建鼓(4件)以及陶埙,同时还出土有钟簴、磬簴。M3现存编镈(5件)和编钮钟(9件)。从乐器种类来看,刘家洼墓地出土的乐器并无特殊之处,但仔细审视这些资料,有些发现却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现场播放了王清雷阐述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学术价值的视频(资料出自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考古进行时)。
王清雷分为九个方面详细阐述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学术价值以及使用刘家洼M1编甬钟和编磬原件试奏的情况。
第一、编甬钟
目前所知,刘家洼M1出土编甬钟10件,M2出土编甬钟12件。编甬钟于口内壁有调音锉磨的痕迹,调音槽有多有少。经现场试奏可知,有的甬钟可以发出清晰的双音,正、侧鼓音的音程关系或为大三度,或为小三度,可以判定为实用器。尤为珍贵的是,M2还出土有钟簴(2架),特别是西侧钟簴保存较好,上有嵌蚌饰的木雕漆绘图案,下伏圆雕兽形簴座甚为壮观。
第二、编磬(及磬簴)
据目前的发掘资料可知,刘家洼M1出土编磬10件,M2出土编磬6件。编磬均为石灰岩质。从器型来看,分为两型,A型为传统的凸五边形磬,M1编磬均属此型,M2部分编磬也为此型;B型为山字形磬,其特点是两博均为弧形。在两博与股上边、鼓上边相交处各有一个折角,与倨句一起大致构成一个山字形,王清雷将其命名为山字形磬,M2出土的部分编磬属于此型。B型山字形磬为首次发现,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学术意义。
第三、建鼓
刘家洼墓地出土建鼓共计5件,其中M1出土1件,M2出土4件。这些鼓有的有鼓座,有的没有鼓座。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鼓身均有一根鼓杆贯中而出。《礼记·明堂位》载:“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悬鼓。”郑玄注:“楹,谓之柱贯中,上出也。”此处所谓的“楹鼓”就是指建鼓。如果按照郑玄所言“柱贯中,上出”的标准来看,刘家洼墓地出土的鼓均为建鼓。刘家洼M2这一座墓葬竟然出土4件建鼓,这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特别珍贵的是,M2出土的一件建鼓铜套上有刻铭10余字,其中2字为“芮公”。
第四、钲
刘家洼墓地出土1件钲。青铜质。钲腔横截面呈合瓦形。平舞,圆柱形甬。甬上有一穿,可以悬挂演奏。器表所饰主纹为减地平雕的饕餮纹。初步判断其应为西周末至春秋初之器,是目前所见有关钲的最早实物之一。现以西周末至春秋初的刘家洼M1钲来看,有的学者认为“钲可能最先出现于中原地区的河南”的推断,仍有商榷的余地。
第五、钟铃与建鼓的组合
刘家洼墓地出土铜铃数量很多,器型多样,有銮铃和钟铃等。在刘家洼M2的东南角发现有4件钟铃与1件建鼓放在一起。根据墓葬出土器物的组合关系,M2的东南角、南侧与西侧均为乐器区。故此,这4件钟铃的功能并非车马器,而为乐器,其应和建鼓配套使用。这种将钟铃与建鼓一起使用的乐器组合,是目前考古首次发现的新现象,再一次刷新了学界的认识。现场播放了刘家洼M2钟铃与建鼓的出土情况的视频(资料出自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
第六、罕见的五音孔埙
目前,刘家洼墓地出土的埙至少有2件,一件为红陶,一件为黑陶。均为五音孔,5个按音孔的布局为前三后二。刘家洼M2五音孔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例出土自墓葬的东周五音孔埙。在刘家洼考古队,王清雷老师带领研究生张玲玲、陆昕怡对2件陶埙均进行了测音,由陆昕怡担任埙的试奏。
第七、不是谜题的谜题——刘家洼M2编甬钟的排序
从发掘现场可知,在M2墓室南侧出土钟簴和磬簴各一架。在墓室西壁出土钟簴一架。当我们站在墓室中间来审视南壁和西壁的两架编甬钟时,会发现其悬挂顺序似乎有误。按照编钟的演奏规律,应该按照音高从低到高的顺序悬挂。从编钟的体量来说,就是应该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悬挂。但是从现场遗迹来看却恰恰相反,两架编钟都是按照从小到大(音高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的,与编钟的演奏规律相悖。从“视死如视生”的角度来看,墓主应该是在棺椁的位置或是床榻的位置来欣赏“金石之乐”,那么乐工就绝对不会站在钟磬(钟簴、磬簴)的内侧、背对国君来演奏,而应是面对国君来演奏。我们从乐工的位置再来审视这两架编钟的排序,其正好是按照音高从低到高悬挂的,完全符合编钟的演奏规律,问题迎刃而解。这也正是民族音乐学所提倡的“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视角问题。
第八、刘家洼M2的乐悬规制
刘家洼M2出土编磬一架,编甬钟两架,可以摆成三面的轩悬之制。但从M2的椁室图来看并非如此,一架编甬钟摆在墓室西面,另外一架编甬钟和一架编磬摆在南面,构成一个两面的曲尺形,属于判悬之制,而不是三面的轩悬之制。那么M2的乐悬规制究竟为判悬还是轩悬呢?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和解读考古材料的问题了。通过综合分析,刘家洼M2的西面、南面应各摆一架编钟,东面应摆一架编磬,可为轩悬之制。刘家洼M2墓主当为一代芮国国君。轩悬之制恰与墓主身份相符。如果分析不谬的话,刘家洼M2的钟磬乐悬为目前所见最早的轩悬(或曲悬)之实例。
第九、刘家洼M1钟磬和鸣
为了配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申报201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应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经理、刘家洼考古队队长种建荣先生的邀请,2019年3月14日至21日,王清雷偕助手张玲玲、陆昕怡和陈健一行4人第二次来到刘家洼考古队,对刘家洼东周遗址出土的乐器做全面的资料采录工作。令人惊喜的是,刘家洼M1出土的一套编钟(7件)和编磬(10件)均可以演奏五声音阶,更出于意料的是二者竟然同为F宫。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王清雷与助手张玲玲、陈健用刘家洼M1编钟和编磬原件试奏了一首乐曲《北京的金山上》,这首乐曲已于2019年5月29日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探索发现》栏目之《刘家洼考古记》(五)中播出,在讲座现场播放了这段精彩视频。钟磬和鸣,金声玉振,在座师生欣赏到2700多年前极其珍贵的芮国国君享用的金石原声。
讲座最后,王清雷指出:目前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出土乐器的详细资料(如文字、数据、测音、图片等)基本采录完毕,正在梳理过程中。尤其是,待编钟、编磬等乐器的测音资料整理后,将对其音列、音准和律制做进一步的研究,届时必定会有更为重要的学术发现。
讲座结束后,老师和同学们就编钟的调音、编钟的测音与分析、钟磬的演奏等诸多问题向王清雷请教,展开了深入的互动与交流。

